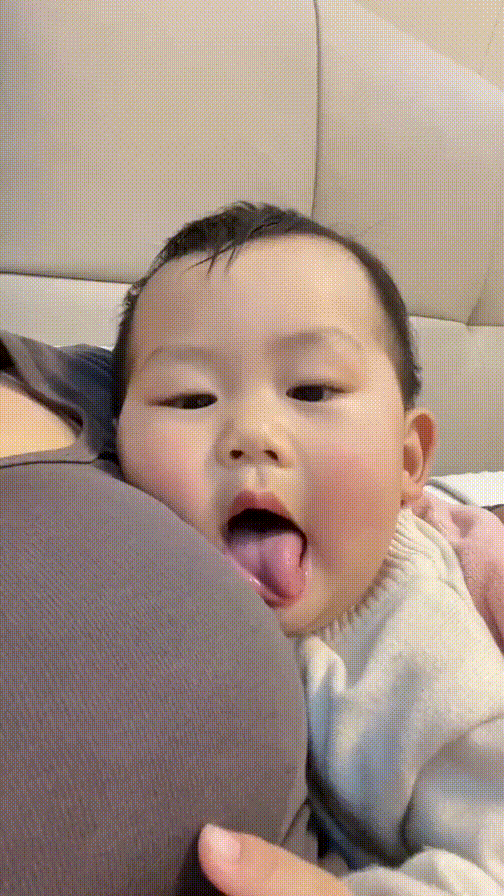95%的AI投资零回报
北京时间周二晚间,美股科技板块遭遇年内最大幅度抛售,纳斯达克指数暴跌。
市场普遍将此次暴跌归咎于麻省理工学院最新发布的AI产业研究报告——《The GenAI Divide:STATE OF AI IN BUSINESS 2025》。
报告指出:95%的企业AI投资实际上未能产生经济效益,被困在“高投入、零回报”的困境中。尽管ChatGPT等通用工具普及率惊人(超过90%的知识工作者日常使用),但企业级AI应用却呈现冰火两重天。科技和媒体行业展现出真正的结构性变革,AI颠覆指数达到2.0;专业服务、医疗与医药、消费零售、金融、先进制造等行业试点多但结构性变化低,指数徘徊在0.5左右;而能源与材料行业却接近零突破。
一位制造业COO在接受调研时直言:“领英上满天飞的AI革命,在我们的工厂里仅仅体现为合同处理速度加快了些,本质上什么都没改变。”研究发现,企业AI项目普遍陷入了“试点陷阱”。虽然60%的企业评估了定制化AI工具,但仅有20%进入试点阶段,最终只有5%能真正进入生产环境。这种断崖式衰减暴露了核心矛盾:员工喜爱ChatGPT的灵活性(83%的试点转化率),却无法忍受企业工具的“机械呆板”。一位企业律师坦言:“公司花5万美元采购的合同分析工具,远不如我自费(每月20美元)的ChatGPT好用——即使供应商声称使用相同的底层技术。
究其根本,当前AI系统的核心缺陷不是模型差,而是“学习缺口”。90%的用户拒绝在关键任务中使用AI,原因惊人一致:“它每次都要重新理解上下文,就像永远培训不完的新员工。”也就是说,大多数AI系统不会记忆与演进,并与真实的流程脱节。当潮水退去,95%的AI投资可能“裸泳”。这份报告揭示的不仅是技术困境,更是企业战略的深度反思——真正的AI革命不在模型参数多少,而能否融入工作流程。对于那些仍在盲目追逐模型参数的企业,或许该先回答一个问题:当95%的同行都在数字化迷雾中迷失方向时,你的AI系统真的具备进化能力吗(NISCI《美股暴跌幕后:MIT揭穿AI投资泡沫,95%企业零回报》)?
他们见到权贵时为什么不点头哈腰?来美国的有些亚洲新贵们,很快就发现他们身边少了一份熟悉的羡慕,便多了一份失落。于是,他们随时分发印有董事长头衔的名片,结果并不管用。于是又一掷千金,买下华屋名车。
可气的是,竟然连那些居陋室,开破车的美国佬也岿然不动,不肯景仰擦身而过的奔驰老总。当然更不会有人注意到他们袖口或领口的名牌。在美国,高薪、华屋、名车的群众号召力没有在新富国家那样大。这个世界上难道还有什么物质比我们自身更令人动心的吗?当然没有。很多美国人身为粗工阶层,也是心满意足。当你出入豪华宾馆时,为你叫车的男孩不卑不亢,礼貌周到,你会感到他的自信。一个访美的亚洲官员讲:“我在国内时别人见我就点头哈腰。可是在美国,连有些捡破烂的人腰板都挺得直直的。”是的,当个人不能威风时,整个民族就可以威风了。我原来工作的办公室里有个维修计算器系统的老美,大学毕业,工作十年了,很平常一个人。处久了,我们每天见面时也调侃几句。一天,我开劝他:“你为什么不去微软工作呢?几年下来股票上就发了。”他说:“我不喜欢微软,这儿好。”后来我发现他有一张合影照片,他、他姐姐、姐夫、比尔盖茨。才知道他姐是早年跟比尔盖茨一起打下微软今天的功臣,现担任微软的副总裁,也是亿万身家了。一问,办公室里有人知道,却没人跟他套交情,大家把他直来直去。他不求致富,有一份淡泊的安祥。在这片崇尚自由呼吸的土地上,当你我理解并尊重他人的选择时,就不会试图用高薪去让一个寻求价值的教授下海,用博士学位去让一个安于现状的蓝领汗颜,用奔驰去让一辆傲然过街的旧车愧退,用华屋去让一位与世无争的近邻气短。信心乃人生之本,舍本求末,难为自己,也难为他人。有一位朋友,拿到一个大学的教授职位,高高兴兴地从麻省来加州赴任,先租公寓房住。自己是教授,住的公寓当然不差。隔壁邻居是一家墨西哥人,每天见面都打招呼。聊天时老墨中气十足,没什么文化,但神色之间透出对生活相当满足的自信(思享无界《为什么美国人见到官员从不点头哈腰?》)。美国是如何失去世界制造业强国的地位的?20世纪初,美国率先采用可互换零件,并组织工厂进行大规模生产。凯斯西储大学经济学家苏珊·赫尔普指出,二战极大地推动了美国制造业产能的提升,同时也重创了其他国家的竞争对手。
20世纪50年代,美国约有35%的私营部门就业岗位在制造业。如今,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为1280万,占私营部门就业的9.4%。战后,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进入中产阶级,推动了对耐用品的消费激增,比如为新购住房添置的汽车和家电。制造这些产品时选择在美国而不是其他国家,是因为要保持技术领先,需要研发团队与工厂紧密协作。
此外, 20世纪初兴起的中学教育运动,使美国拥有世界上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劳动力,也为制造业发展提供了支撑。赫尔普解释道: “当你变得更富裕,你能就业也随之转移,越来越多的人为服务业企业工作,比如酒店、银行、律所和医院。尽管期间有经济衰退和复苏的波动,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制造业就业总体保持平稳,而服务业就业不断增长。买的车有限,接着你开始消费服务。”在表面之下,美国人购买的许多非耐用品(如服装)的产地也发生了变化。大量生产转移到了美国南部各州,那里的劳动力成本更低。与此同时,拉丁美洲和亚洲等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地区开始加大非耐用品的制造。美国开始越来越多地进口这些产品。随着时间推移,这种趋势也蔓延到轻型耐用品,比如搅拌机。
20世纪80年代起,情况开始发生变化。美国非耐用品制造商在与低工资国家的竞争中越来越难以为继。但相比之下,80年代和90年代的变动都不及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冲击。中国向外国投资开放市场,并获得进入全球市场的渠道。美国过去也曾面临来自其他国家的进口竞争,但都不是人口远超自己的国家。而且中国的崛起速度远远快于日本等国。
1999年,中国商品出口总额仅为美国的十分之一,甚至还不如瑞典。但到了2008年,中国就超越美国,成为全球商品出口第一的国家。随着中国制造的商品越来越多,美国则在服务领域变得更加熟练(镜子里的财经《美国如何失去世界制造业强国的地位,特朗普关税能做到什么?》)
赞(17)